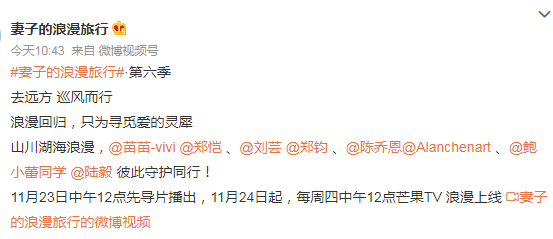哲学在什么地方会停止呢?哲学力图要把这个世界说明白,不管是《论语》,还是《道德经》,都力图把世界深处的道理说明白。哲学说不清的事是哪些事呢?比如人的内心、人的情绪、人的情感、人的私心、人的思考和人的灵魂,都是哲学永远说不清楚的。哲学说不清这些事谁来说?文学。赫拉克利特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你永远找不到灵魂的边界,即使你找遍所有道路,也是如此。因为它的原因隐藏得非常之深。
◤文学中的“目光”:介入者与出走者◢
另外,文学中是有“目光”的。比如鲁迅先生,他跟他同时代的作家有很多区别,特别是和他同时代的乡土文学作家——当然他们也写得非常好,但他们写的就是乡土文学,而鲁迅先生写乡土写出来的是世界性的作品。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并不是鲁迅先生对农村的生活比那些作家更熟悉,而是鲁迅先生作品中的目光和其他乡土作家的目光是不一样的。其他乡土作家是从一个村来看世界,鲁迅先生是从世界来看一个村庄,所以他就写出了像阿Q、祥林嫂、孔乙己这样的人物。
就我自己而言,写到《一句顶一万》的时候,感觉稍微开窍了一点。《一句顶一万》写的是一些不爱说话的人,比如与卖豆腐的、杀猪的、剃头的、染布的、破竹子的,还有传教的。我们村的人都不大爱说话,包括我也不爱说话,因为他说话不占地方,他说话也没有人听,他把对话变成了自言自语,久而久之在尴尬和自嘲的情形下,他也就不说话了。
但不爱说话并不是说他没有话。那他的话哪里去了?他的话被咽进去了。过去有一句话说“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打碎了的话也在往肚子里咽”。不爱说话到了肚子里就变成了心事,那么多不爱说话的人都在大街上走,万千心事汇成万千洪流,改变着生活,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这是一个哲学的辩证思考。
《一句顶一万句》里我写了传教士老詹的故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确实有很多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其中一个传教士来到了河南延津,他是意大利米兰人。意大利人的名字都特别长,延津人嫌麻烦,叫他老詹。老詹来的时候眼睛是蓝的,黄河水喝多了,就变黄了;来的时候,鼻子是高的,但老在河南吃羊肉烩面,就变成了一个面团。四十年过去了,老詹在街上走,背着手,和一个卖葱的老头没有任何区别。他来到我们延津四十年就发展了八个信徒。
他在黄河边遇到了一个杀猪匠老曾,就说,老曾你信主啊。
老曾说,信主有什么好处?(这是中国人的思考习惯)
老詹说,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老曾说,不信我也知道,我是老曾,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
老詹说,你说得也对,那你总不能说,你心里没忧愁吧。有忧愁你不找主找谁呢?主马上告诉你你是个罪人。
老曾又急了,我跟他一袋烟的交情也没有,咋知道错就在我呢?
老詹的教堂后来被县长征走了,他就住在一所破庙里,每天给菩萨上炷香:菩萨,保佑我再发展一个教徒。他心中的教义无处诉说,每天晚上用意大利文写信,写给远在米兰的他妹妹的孙子。正因为他在延津把主的福音说出来了,所以他对教义的理解非常深刻。这些深刻和独到的理解,漂洋过海回到米兰,进入一个八岁孩子的世界。八岁孩子觉得老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传教士,他的信徒有几千万,他的教堂一定像米兰大教堂一样雄伟。老詹去世了,那些杀猪的、磨豆腐的、剃头的去给他办丧事,发现一张图纸,就像米兰大教堂一样宏伟的延津第二教堂的图纸。这时候,图纸活了,塔顶上的大钟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老詹确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传教士,他传教没传给别人,但传给了他自己。什么地方最适合传教,在不信教的地方。这个地方,有老詹的介入和没有老詹的介入是非常不同的。
《一句顶一万句》出法文版的时候,我去法国一个书店交流。一个法国女士站起来说,你知道我们老詹他妹妹的孙子现在干什么?我说不知道,因为他在书里就是一个收信的小孩。那位女士说,他现在就是米兰大教堂的大主教。听了之后我特别震撼,也特别自责,觉得《一句顶一万句》没有写好——哲学和文学的量子纠缠在我这里出现了。如果我当时能知道有这样的人物结构、知道八岁小孩未来成为了米兰大教堂的大主教,如果我当时有这样的视野和格局,《一句顶一万句》又不一样了。
所以孔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吾日三省吾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对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是对的——但确实存在着不同的“道”。当你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你肯定是想把它写好,但是你回头看也会有很多遗憾。当然缺点并不是坏事,失败也不是坏事,它是写下一部最大的动力。
◤不是死了三百万人而是一个人死了三百万次◢
最后,我想谈谈幽默。全世界都知道我很幽默,那是他们没到我们村去——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幽默分很多层面:首先,是语言的幽默,但我的作品里没有一句话是幽默的,而是后面的故事结构和人物结构的幽默。当然,最好的幽默是结构背后道理的幽默。
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写了河南饥荒那么大的灾难,但能够看到这个小说里的幽默。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生活背后的道理就很幽默。1942年因为旱灾和国民政府赈济不力等原因,河南死了三百万人。我认为,用哲学的理论来解释,其实不是死了三百万人,而是一个人重复死了三百万次。死了三百万人是一个事实,一个人死了三百万次是一个思考。因为这三百万人的死法、原因、动因,包括最后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能让一个事在同一片土地上重复三百万次,而且是死亡,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用这种幽默的态度来对待三百万次的重复死亡?
在写小说之前我回了老家,想问问1942年的幸存者,比如我的外祖母。我说,姥姥我们聊聊1942年。1942年是哪一年?饿死人那一年。饿死人的年份太多了,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遗忘比残酷更触动我。人对恐惧的恐惧是一种恐惧,对恐惧的遗忘是另一种恐惧。
行,我说为了遗忘我就试试吧。接着我就把从1940年到1945年的世界范围内的文献都看了,包括《泰晤士报》《民国日报》,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文件等等。看完之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大和小”之间的哲学问题:对一个区域来讲,三百万人很重要,特别对我们河南人而言;但是1942年发生了很多事:斯大林格勒战役、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等等,从《纽约时报》一直到《泰晤士报》,所有世界的新闻都集中在了斯大林格勒,集中在了宋庆龄访美,集中在了甘地绝食。有报道说丘吉尔感冒,却没有一个小豆腐块在说河南,那就证明河南死了三百万人,在世界的格局中是不重要的,对蒋委员长也是不重要的,他需要处理的是跟美国、英国、苏联之间的关系,包括进入胶着状态的中日战争——那些事情稍微处理不好,中国就会向别的方向偏离。但在内地死了三百万人,不会影响世界的格局。我突然发现他们不是因为旱灾饿死的。
 《春闺梦里人》今日开播 丁禹兮彭小苒逗趣
《春闺梦里人》今日开播 丁禹兮彭小苒逗趣 《人生之路》引热议,总制片人魏巍谈改编—
《人生之路》引热议,总制片人魏巍谈改编— 李奕臻综艺现场成“神助攻” 演员间的“淋
李奕臻综艺现场成“神助攻” 演员间的“淋 《三孩来了》张亮承认对儿子女儿双标 范世
《三孩来了》张亮承认对儿子女儿双标 范世 京剧摇滚碰撞《披荆斩棘的哥哥》舞台,点燃
京剧摇滚碰撞《披荆斩棘的哥哥》舞台,点燃 《当爱已成往事》等5部南斯拉夫经典影片将
《当爱已成往事》等5部南斯拉夫经典影片将 吴京再现扛红旗名场面!这一次,他骑着烈马
吴京再现扛红旗名场面!这一次,他骑着烈马 百位明星健康宝照片外泄 窥私应该有底线
百位明星健康宝照片外泄 窥私应该有底线 大牙出庭陈建州诉其妨害名誉案 呼吁
大牙出庭陈建州诉其妨害名誉案 呼吁 台媒曝李玟告别式7月31日举行 李玟二
台媒曝李玟告别式7月31日举行 李玟二 吴宗宪女儿吴姍儒宣布怀孕晒b超照分
吴宗宪女儿吴姍儒宣布怀孕晒b超照分 港媒曝黄心颖结婚 与大14岁男友申请
港媒曝黄心颖结婚 与大14岁男友申请 《这!就是街舞》第六季官宣队长吴建
《这!就是街舞》第六季官宣队长吴建 传李小璐11月生产 挺大肚与贾乃亮甜
传李小璐11月生产 挺大肚与贾乃亮甜 王子腾新剧《宁安如梦》正在热播 反
王子腾新剧《宁安如梦》正在热播 反 94版《三国演义》关羽饰演者陆树铭去
94版《三国演义》关羽饰演者陆树铭去 英王妃凯特表妹夜店狂欢 全裸跳脱衣
英王妃凯特表妹夜店狂欢 全裸跳脱衣 《废柴联盟》电影正式开始运作“six
《废柴联盟》电影正式开始运作“six  布兰妮父亲病重入院 其或将得到父亲
布兰妮父亲病重入院 其或将得到父亲 《越狱》执行制作人猝死 年仅51岁
《越狱》执行制作人猝死 年仅51岁 YG娱乐股价时实暴跌 回应LISA不续约
YG娱乐股价时实暴跌 回应LISA不续约 日本女星石田桃子疑似在家中被活活热
日本女星石田桃子疑似在家中被活活热 韩媒曝全智贤-宋慧乔片酬一集2亿韩元
韩媒曝全智贤-宋慧乔片酬一集2亿韩元 EXO灿烈个人单曲《Good Enough》在iT
EXO灿烈个人单曲《Good Enough》在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