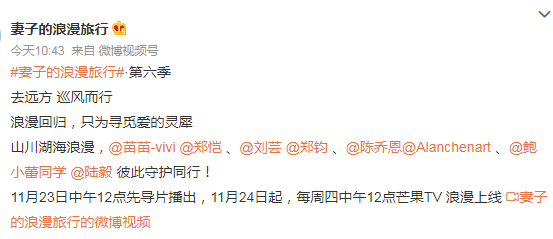play stop
mute max volume
repeat
文学经典作为戏剧的改编对象,历来并不鲜见。然而,由于舞台演出的时长有限,当面对几十万字甚至几百万字的文学巨著进行改编时,通常采取的做法是取其中一个或一组主要人物,或者取其中一个或几个主要事件,以此为核心进行比较深入的改编。以《红楼梦》为例,越剧的经典之作《红楼梦》,就是以宝黛爱情为主线,兼顾家族内部的其他矛盾展开;昆曲《晴雯》和京剧《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等也都属于此类作品。
对于鸿篇巨制做大体量、全景式的改编,则是近几年国内外话剧领域出现的新现象。除了上下两场共六小时的《红楼梦》之外,我们还看到了时长近四小时的话剧《尘埃落定》以及时长八小时的俄罗斯话剧《静静的顿河》、时长九小时的法国剧团改编智利作家的《2666》等,业界称之为“马拉松戏剧”。与局部性改编相比,这样的改编显然更能展现文学巨著广阔而相对完整的面貌,以及与之相符合的戏剧表现方式,对于观众来说,也提供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观看体验。
这种趋势的出现,和戏剧观念的变化有关,即与当今戏剧界重提戏剧的文学性的问题有关。
戏剧界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非常注重“实验性”的探索。一些实验戏剧热衷于挑战戏剧文本的基础性地位,认为戏剧的本质是通过现场表演传达的,故而不应拘泥文学性。在西方,激进的残酷戏剧的创始人阿尔托主张戏剧要“结束戏剧从属于剧本的状态”,代之以“在空间中表现”的新的戏剧语言;格洛托夫斯基坚持戏剧只是“发生在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事”,其他都是附加的东西,因而要创立“贫困戏剧”;德国的雷曼则以“后剧场戏剧”的定义来强调此种观念。这些理论影响所及,在有些戏剧从业人员眼里,戏剧的文学性被视作是老派过时的代名词。
然而在经过长期的实践与理论的探索验证之后,今天的戏剧界越来越辩证地重新认识到,文学性对于戏剧的内涵深度、人文价值极为重要。许多戏剧家大声呼吁要让文学性重回话剧舞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不少长篇文学名著纷纷进入戏剧界的改编视野,包括陕西人艺的茅盾文学奖改编本三部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主角》等,体量都很可观。文学名著可以使得戏剧作品的内在张力更足,戏剧也能够使得文学名著以另一种形式得到表现和传播。这些舞台作品的出现,既是创作者们希望用当代视角看待文学名著、以戏剧手段传达文学精神的努力,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戏剧的社会功能和艺术特征的理解日益全面,戏剧观念、戏剧思维更加丰富。
当然,和一般的文学作品改编不同,如《红楼梦》《静静的顿河》这样大部头的经典名著,其全景式的舞台改编全面考验着编导的艺术功力。概括而言,起码有三个问题关系到作品内涵的传达和观众的审美体验,需要解决。
首先,文学名著内在的精神、内在的气质、内在的文学的风格,能不能在戏剧作品里得到真正的体现?每一个改编者都有自己对于原著的理解,有自己再创造的视角和方法,可能有的改编还原度更高,有的改编创新性更强,这些都没有问题,但如果改编的结果是丧失了原著的气质和精神,那就不能算成功。一流的文学作品之所以难以改编,正因为其具有非常强烈的只属于自身门类的特质。而所谓“忠实原著”,并不是狭义地要求故事、人物、台词的照搬,而是要把握原著的内涵和精粹,把它用戏剧手法准确地体现出来。这需要改编者对于原著有真正深入的研究和了解。
其次,长篇巨作不仅故事复杂、人物众多,所展现的社会面也更加广阔,相应的,改编之后一定会需要更多的戏剧场景来表现,如何使其形成一个逻辑统一、主次分明、详略得宜、错落有致的艺术整体?无论是话剧《尘埃落定》还是话剧《红楼梦》,都采用了比较灵动的叙述方法:《尘埃落定》是以傻子少爷的成长和叙述来贯穿,并且有意识地保留了原著小说里的语言风格;《红楼梦》除了以贾宝玉的视角为主,他人的视角为辅,串起宝黛的爱情、十二金钗的命运以及荣国府宁国府里种种道貌岸然下的虚伪之外,还采用了一些对称的手法,比如将两次中秋赏月和诗会及元春的省亲和去世对称安排在上下半场以形成对比和呼应。这样的结构方法,都是希望能流畅自如而又线索明晰地铺叙作品的生活面与人物众生相。相比之下,《红楼梦》因为体量更大,难度也更高,全剧的总体把握未来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第三,中国传统戏曲比较习惯于处理一人一事的故事,但长篇文学作品的大体量改编必然要面对人物众多的问题,如何在舞台上构建一个琳琅满目的人物长廊,展现出他们独特的性格、形象和命运,让观众能够清晰地辨认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而不是演员在台上演了半天观众都不知道谁是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因为人物多了,分在每个人身上的笔墨必然少了,需要用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人的特点并且使其传神,还要在他和其他人物之间建立起立体的关系。很多观众在看了话剧《红楼梦》之后,觉得贾母、王熙凤、刘姥姥等几个人物形象比较鲜明生动,相比之下,十二金钗的大部分形象艺术特征尚不够明显,需要通过台词来进行辨认。这中间有文本提供的戏份的原因,也有演员艺术创造力表现力的原因。俄罗斯话剧《静静的顿河》也有类似的情况。
由此可见,大体量文学名著的改编对于编剧、导演、演员、舞美等各个环节都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你面对的不是一个相对集中的形象,而是比较宽阔的画面和厚重的人文价值,需要创作者将自己的文学修养和戏剧能力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把纸面上的人物转变成舞台上的形象。这些舞台形象是你创造的,同时又是作家所创造的文学形象最为传神的表达。
从以上角度来看,话剧《红楼梦》的许多艺术处理是颇有成效的。其中有两场戏我特别喜欢,即上半场的“刘姥姥一进大观园”和下半场的“抄捡大观园”,其场面和人物关系的戏剧性与人物形象的鲜明表达,以及内在的意义都体现得比较出色。
“刘姥姥一进大观园”,在原著中就有把贾府的奢靡繁盛矫饰与刘姥姥的窘迫粗鄙莽撞做对比的意味,转换到戏剧舞台上,首先是演员非常生动地把一个农村老太太的朴实以及她跟大观园的格格不入表现了出来。而一个品尝茄鲞的细节,王熙凤不经意间夸耀贾府食不厌精的奢靡和刘姥姥为之咋舌的自嘲,便凸现了上半场编导渲染的“风月繁华”的基调。更有意味的是,话剧把王熙凤托付巧姐儿提前到了这一幕,宴席散场,在贾府呼风唤雨的王熙凤向这位看似不上台面的刘姥姥吐露了担心女儿未来命运的隐忧,请求她将来能保巧姐儿平安。这不仅是因为篇幅原因而做出的结构调整,更是一种隐喻,一种反讽:看似风光无限的王熙凤内心的孤独,表面烈烈轰轰的望族私底下的不安,皆在其中。这一幕兼具丰富的戏剧表达和内在含义,是曹雪芹原作精神的舞台呈现。
 《春闺梦里人》今日开播 丁禹兮彭小苒逗趣
《春闺梦里人》今日开播 丁禹兮彭小苒逗趣 《当爱已成往事》等5部南斯拉夫经典影片将
《当爱已成往事》等5部南斯拉夫经典影片将 《三孩来了》张亮承认对儿子女儿双标 范世
《三孩来了》张亮承认对儿子女儿双标 范世 吴京再现扛红旗名场面!这一次,他骑着烈马
吴京再现扛红旗名场面!这一次,他骑着烈马 《人生之路》引热议,总制片人魏巍谈改编—
《人生之路》引热议,总制片人魏巍谈改编— 京剧摇滚碰撞《披荆斩棘的哥哥》舞台,点燃
京剧摇滚碰撞《披荆斩棘的哥哥》舞台,点燃 百位明星健康宝照片外泄 窥私应该有底线
百位明星健康宝照片外泄 窥私应该有底线 李奕臻综艺现场成“神助攻” 演员间的“淋
李奕臻综艺现场成“神助攻” 演员间的“淋 大牙出庭陈建州诉其妨害名誉案 呼吁
大牙出庭陈建州诉其妨害名誉案 呼吁 吴宗宪女儿吴姍儒宣布怀孕晒b超照分
吴宗宪女儿吴姍儒宣布怀孕晒b超照分 港媒曝黄心颖结婚 与大14岁男友申请
港媒曝黄心颖结婚 与大14岁男友申请 台媒曝李玟告别式7月31日举行 李玟二
台媒曝李玟告别式7月31日举行 李玟二 94版《三国演义》关羽饰演者陆树铭去
94版《三国演义》关羽饰演者陆树铭去 王子腾新剧《宁安如梦》正在热播 反
王子腾新剧《宁安如梦》正在热播 反 传李小璐11月生产 挺大肚与贾乃亮甜
传李小璐11月生产 挺大肚与贾乃亮甜 《这!就是街舞》第六季官宣队长吴建
《这!就是街舞》第六季官宣队长吴建 《越狱》执行制作人猝死 年仅51岁
《越狱》执行制作人猝死 年仅51岁 英王妃凯特表妹夜店狂欢 全裸跳脱衣
英王妃凯特表妹夜店狂欢 全裸跳脱衣 《废柴联盟》电影正式开始运作“six
《废柴联盟》电影正式开始运作“six  布兰妮父亲病重入院 其或将得到父亲
布兰妮父亲病重入院 其或将得到父亲 韩媒曝全智贤-宋慧乔片酬一集2亿韩元
韩媒曝全智贤-宋慧乔片酬一集2亿韩元 YG娱乐股价时实暴跌 回应LISA不续约
YG娱乐股价时实暴跌 回应LISA不续约 日本女星石田桃子疑似在家中被活活热
日本女星石田桃子疑似在家中被活活热 EXO灿烈个人单曲《Good Enough》在iT
EXO灿烈个人单曲《Good Enough》在iT